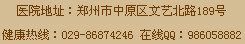![]() 当前位置: 甲型病毒性肝炎 > 疾病治疗 > 张起ldquo五津rdquo寻踪
当前位置: 甲型病毒性肝炎 > 疾病治疗 > 张起ldquo五津rdquo寻踪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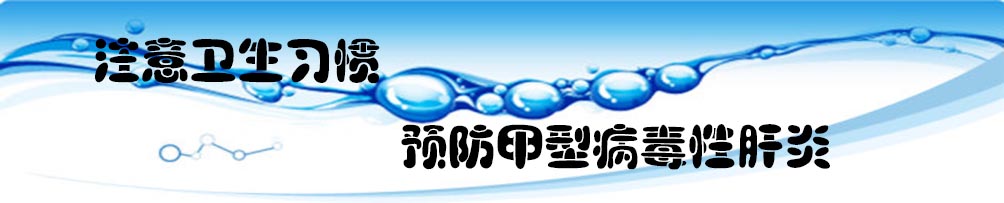
![]() 当前位置: 甲型病毒性肝炎 > 疾病治疗 > 张起ldquo五津rdquo寻踪
当前位置: 甲型病毒性肝炎 > 疾病治疗 > 张起ldquo五津rdquo寻踪
初唐王勃被高宗废黜后,曾客剑南,在此完成了其名作《杜少府之任蜀州》,后世影响极大,原诗是:
城阙辅三秦,风烟望五津。
与君离别意,同是宦游人。
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。
无为在歧路,儿女共沾巾。
这首诗有几处疑点,即诗题、五津、蜀州。笔者认为解答“五津”为首要,它是打开所有疑窦之钥匙。“五津”确切的范围,必须辩明,它可解开杜少府往任之所,也可判定送人的出发地是在成都而非长安,进而可辩明“蜀州”与“蜀川”的正讹。
前代与近代学者钱谦益、陈寅恪“以史证诗”,“文史互证”的治学方法,给我们启示,在理解古人时,必备基本文史知识,以古人的生活环境去揣摩还原。但今人理解“五津”之误区,往往以现代地域观念,甚至行政区划去解释,或采古人材料,以今人的地域思维,去穿凿古代的地域范围。如广有影响的《文学评论》刊载了《蜀川与蜀州辨考》。
该文一是“揆诸史实”,蜀州设于王勃死后十年,故诗题不可能称用“蜀州”;二是臆测“似‘蜀川’一名其地理范围就是指嘉州之地”,川中乐山,这样杜少府往任之所就在乐山,五津就扩大到了今乐山犍为;三是既已认定蜀川为乐山,却又矛盾地判定诗题“‘蜀川’就是指蜀郡”,“秦灭蜀,改置为蜀郡,郡治即在嘉州”,众所周知,蜀郡就在成都,因此作者为了自己错误的历史地理逻辑,又不合史实地穿凿出“后移到成都”;四是针对近人有诗题“蜀州”为“眉州”之讹的说法,作者又认为“虽不能说没有道理,然迂回改字,故所不取”。
从以上几点看出作者并不了解蜀郡和蜀州的历史,以为蜀郡原在嘉州,“蜀川”亦在乐山一带,这样就把诗圈定在乐山,相应地,作者也就认为近人蜀州为眉州之误也是不无道理的,只是不该改字。对此,笔者认为正确的做法是,以古代地域观念、材料去详加稽考、还原。
唐诗注本注“五津”一律采用《华阳国志·蜀志·蜀郡》卷三材料:
“其大江自湔堰下至犍为有五津:始曰白华津,二曰里津,三曰江首津,四曰涉头津,五曰江南津。”
许多论者多结合今日行政区划地图加以推测,如上述《蜀川与蜀州辨考》的作者就把“五津”从灌县(今都江堰)推至今犍为的疆域,扩展至数百里,找一些材料穿凿比附,纸上谈兵,进而认定诗题当然是“蜀川”,泛指今乐山一带,而非“蜀州”了。这是因为对“五津”范围妄加扩大的错误。甚至连“普通高等教育‘九五’国家级重点教材”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》(郁贤皓主编)也犯了三个错误,一是语焉不详,“五津:岷江从灌县到犍为县间的五个渡口。”解释或已扩大到今乐山境内;二是教材的诗题用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川》,显然割裂了“五津”与“蜀州”的关系,他们或许不知道“蜀川”与诗中的“五津”没有任何关联;三是认定送杜少府“时王勃在长安”,为什么不能在成都送人呢,显然“长安送人”说,还缺乏令人信服的必要证据。笔者认为仅利用旧材料,作想当然推考,也是不靠谱的,如果他们能作实地考察,或会修正盲误,改变观点。笔者作为崇州人,常年往返于崇州、新津一带,十分熟悉实情,结合史料作了实考。
“五津”在哪里?应在古江原县境内,从今崇州市至新津县的金马河(岷江)段,约为七十里范围,因为江原县包含了岷江中段的全部水系,也可以说江原依傍岷江而成。
一
从蜀州历史沿革及辖地范围,证明蜀州与王勃诗题“蜀州”有密切关系,而今人行用的“蜀川”泛称之说,根本是不解蜀地史情的无稽妄谈。
笔者参考了蜀学大师王文才先生的《六朝江原故址及侨置郡县考》,又对《崇庆县志》《新津县志》材料作了认真爬梳。崇庆县(今崇州市)《元和郡县图志》“蜀州”总叙云:“《禹贡》梁州之域,秦灭蜀为蜀郡,在汉为郡之江原县也。李雄据蜀,分为汉原郡,晋穆帝改为晋原郡。后魏平蜀后,移犍为郡理此东三十里,因省晋原郡以并之。”可见,秦灭蜀后置蜀郡于成都,崇庆则为蜀郡近邑。汉高祖元年,割大江(按:金马河)以西和今大邑县苏场以北地置江原县(治所今江源乡大庙村)。江原就是今崇庆县建置的初始雏形。可见汉江原县与成都之隶属关系。遗憾的是国内有人在辩蜀州与蜀川之争时,竟把唐蜀州(汉江原县)与成都首府(汉蜀郡)等同看待,认识本已错误,又拿来辩误,怎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呢?省外一些学者在研究王勃诗时,不知唐蜀州就是今成都近郊的崇庆县,自汉就归成都管辖,“蜀州”并非首府蜀郡之改名。因此有必要对汉江源、唐蜀州、宋崇庆的来龙去脉和地域范围作一梳理。
关于江原,东晋常璩最为权威,他即蜀郡江原县人,其《华阳国志》载“后有王曰杜宇,教民务农,一号杜主。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,宇悦之,纳以为妃。移治郫邑,或治瞿上。七国称王,杜宇称帝,号曰望帝。”郦道元《水经注》也载:“望帝者,杜宇也,从天下。女子朱利自江源出,为宇妻。遂王于蜀,号曰望帝。”两书所称“江源”,即今崇庆县。《县志》说,“原”与“源”通,时因误以为县域位于岷江之源,故名。江源即江原。
王文才先生据《南齐书·州郡志》考证,六朝时,江原县曾改汉原郡、晋原郡、晋康郡,领县有江原、临邛、晋乐、徙阳、汉嘉。从文才先生考证可见,江原管辖甚广。蜀郡江原作为常璩故乡,他最为熟悉,在《华阳国志》中记载江原的“五津”亦定是准确的,“大江自湔堰下至犍为有五津”“五津”在江原境内确凿无疑。但今人则多以今天行政区划去看待古人的地域,故认为犍为在数百里外的乐山以下。在这里常璩所云的“犍为”即在江原辖区内。何以确定常璩所云“犍为”不是今天乐山犍为呢?
又据王文才先生考证,西魏据蜀()时,在江原县地侨置犍为郡及僰道县,新置多融县于境内原徙阳侨县旧地。故犍为郡领多融、僰道二县。犍为郡隶东益州,在江原县治内(见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)。这种侨置说明,一是“犍为”东晋时就在新津境内,而江原历来领新津;二是证明江原范围实在广阔。到北周初,犍为郡又加领新津县及清城县(今都江堰市徐渡乡)。
隋朝开皇三年(),悉罢诸郡,以州统县;大业三年(),又改州为郡,益州复称蜀郡,江原县仍隶蜀郡(《隋志》)。笔者认为王勃生于年,时逢郡改州,州复改郡,因此在诗题中采用“蜀州”又未尝不可能呢。针对今人异议“蜀州”为“蜀川”之误,所持均为则天垂拱二年()才置“蜀州”,而王勃已亡故十年,不可能预知未来,故辩为“蜀川”才对。查“蜀川”在古时并不行用,且太泛指,王勃连送朋友所往都不知吗?结合诗中“五津”来看,地点是确指的,就在蜀郡之江原界内,故有可能按时行的州、郡杂称来称“蜀州”,而没有理由去用最不行用的“蜀川”。今人认定为“蜀川”的理由,还出自宋人李昉《文苑英华》的王勃诗题中的“蜀川”,笔者认为李昉未必正确。王勃的“五津”已点明杜少府往任,而江原又属蜀郡,故用“蜀州”指称江原是可以的。我们不可因垂拱二年()才设蜀州而否定其不可用“蜀州”。另外,明嘉靖张逊业《校正王勃集》(两卷本)、崇祯张燮《王子安集》二人根据考证,均作“蜀州”,这是古人常用的以后地名(蜀州)命前地名(江原县)的手法。明人杨慎《丹铅录》亦说:“唐人皆指蜀州(含今崇庆、新津、都江堰、岷江西岸下至彭山江口)为‘五津’。”蜀州正是金马河贯穿,唐人去晋不远,当有所承。故诗题的“蜀州”才是正解。
武后垂拱二年(),分益州置蜀、彭、汉三州。蜀州即今崇州市,领晋原、唐隆、清城(开元十八年易清城为“青城”)、新津四县。故,这就是今人以为诗题不能为“蜀州”之时间断限的理由了。
以上沿革材料证明,蜀州(汉江原县)流变及所领范围广阔,理应包括域内岷江流域的五津。故诗中“五津”即为杜少府行经望达和任职之地。
二
再从新津历史沿革及与蜀州的隶属关系,证明新津地界的犍为郡在蜀州境内,结合《华阳国志》云“大江自湔堰下至犍为有五津”,五津正好在境内,与王勃诗中“五津”相合。
要确定“五津”仅在今崇州至新津岷江河段,还要确定《华阳国志》中“犍为”所在。“犍为郡治”即为后来的新津县治。常璩生于年,主要活动于东晋成汉政权时期,而此时新津尚未建县,其地界正是犍为郡治,故常璩所指犍为即为后来的新津。
犍为建郡,据《华阳国志》载:“汉武帝建元六年(前)开西南夷,分巴、蜀,置犍为郡”,道光版《新津县志》又载:“元鼎二年(前)置武阳县,属犍为郡”,新津地域当时称武阳县,武阳县城大约在今彭山江口附近。道光版《新津县志》又载:孝昭始元三年(前84)以“南夷数叛”,郡治移至武阳。故,犍为郡在今新津境内无疑。
后经东汉、三国、晋、刘宋,近五百年间,犍为郡治在武阳县未变。可见常璩生活的东晋时期,犍为郡就在今新津,而不在今乐山的犍为。
梁武帝大同十年()改犍为郡南部为戎州,改武阳县为犍为县,并在原犍为郡北部(今彭山、新津境)置江州,领犍为一县(《四川郡县志》卷三);西魏时于江原郡(今崇州界)侨置犍为郡及僰道县(《四川郡县志》卷五)。从历史沿革看,常璩所指的犍为就在今新津境内,并且后来还侨置江原郡(文才先生已考订),似为包容关系。
再说新津,汉时由犍为郡城至成都有水陆二路。水路即溯岷江而上。陆路有二道,一是自郡城(即原武阳县城,今彭山县城西北)翻牧马山到成都南面石羊场一带;另一道为平路,即由郡城沿岷江西岸北上,在今新津邓公场渡沙头津(按:疑为常璩所言的涉头津)、皂里津到岷江东岸,再循牧马山麓东北行,经双流至成都南门。明、清之驿路,今之公路大体沿此走向,但此路需跨汉安桥,渡皂里江,“汉安桥(索桥)广一里半,每夏秋水盛(索桥)断绝,岁岁修理百姓苦之”,“皂里江,水急多漩,舟渡最难”,“建安二十一年()太守李严乃凿天社山循江通车道,省桥三津,吏民悦之”(《华阳国志》),道路辟通后,在蒲水、文井江、皂里江之间形成一个新渡口,沟通了成都平原与眉嘉平原两个富庶区域。新渡口于五津汇流处形成集市,时称“新津市”,为新津前身。北周孝闵帝元年()犍为郡治(侨置)亦迁泊于此。新津与犍为之关系,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载明:“新津本汉犍为郡武阳县也,故城东七里”。
以上沿革材料可证,常璩“大江自湔堰下至犍为”的范围就在蜀州地界,“五津”也包含在内,亦杜少府的往任之所。故,犍为并非当下学者认为的今天的乐山犍为县。
常璩《华阳国志》的“五津”就在崇州至新津之间,最远可至今彭山江口镇。历史变迁,至清代这一段岷江还有五大渡口,青城渡(徐渡)、苏家渡(含陈家渡、晏家渡)、三盛渡(三渡水)、江原渡(擦耳岩)、新津渡,清代的这五津还是在今崇州与新津一线。
三
从王勃诗与成都周边的关系紧密来看,送人应该就在成都,而非传统的长安送人之说。这样就可对杜少府行经路线解密、诗题解谜、系年解疑。
江原(蜀州)与新津县的隶属关系、新津县与犍为郡的重合关系,犍为与江原的侨治关系,可确定“五津”的范围,就在江原县治内。而且诗的前后关系“城阙辅三秦”,是成都与周边的关系,“风烟望五津”,则蜀州境内的“五津”与成都的距离也不会很远。王勃在诗中用“五津”是古地名,当指杜少府往任之所就在江原界内的某一县(按:前已述及,江原领县较多)。这样,诗题“蜀川”与“蜀州”之辩可定矣,蜀州即五津,诗题用“蜀州”与首联“五津”互为照应确指,若诗题用作“蜀川”,与“五津”则无必然关联。
确定五津在蜀州境内,杜少府往任之所也就在蜀州境内的某县,故而王勃送人之地就在附近之成都而非长安,诗题当然是“蜀州”。经推测杜少府的行程极有可能出成都西门,过“五津”之首“白华津”前往蜀州属地的。“白华津”可能就是今温江三渡水,自古此为成都至江原(今崇庆县)大路之渡口,清康熙前成都至崇州、邛州驿路均由此渡。过了“白华津”就是蜀州地界,杜少府就在蜀州辖县内任职。故有诗人“风烟望五津”的描写。
这样,我们再来研究王勃此诗题作《杜少府之任蜀州》,历代注家都以为,王勃此诗必作于长安,因长安以三秦为辅,帝都气象,诗中“城阙辅三秦”已点明,送友必在于此;还认为王勃在京城高第,授朝散郎,署沛王府,正是十几岁时,此诗气象壮阔,毫不悲啼,也正是在长安送友人。笔者认为定为王勃早年长安英姿勃发送人是不正确的。观王勃入蜀后的诗文仍然勃勃英气,没有因沛王府斗鸡事件而消沉,二十多岁的王勃正风华茂盛,虽遭挫折,在成都送友不会“儿女共沾巾”。故,定于长安送友有谬,原因有二:一是王勃若没有游蜀经历,何以熟悉蜀地风候?二是清代早有人疑,在长安送人,何以能望见五津,站在长安城楼望风烟中的五津不可思议。笔者认为在成都楼头望五津是可能的,五津就在成都左近之江原,诗中“城阙”是成都,不是特指长安。考“城阙”一词,《说文》云:“阙,门观也。”何注昭公二十五年《公羊传》云:“天子外阙两观,诸侯内阙一观”。证明“城阙”非帝王居地专指。而王勃的诗集中,“城阙”也多次出现,并非专指长安,例如他在四川有《梓州玄武县福会寺碑》:“金堤迥邑,玉峡长澜;城阙纷乱,江山耸盘。”既然在成都送友,何以“城阙辅三秦”呢?因为成都城规模宏大,堪比长安,扬雄《蜀本记》云:“蜀王据有巴蜀之地,本治广都樊乡,徙居成都者也。巴与蜀雠,求救于秦,秦惠王二十七年遣张仪与司马错等来蜀,遂置蜀郡,仪筑成都,以象咸阳。”证明成都自古即以都城规模建筑,与秦相辅,有“辅车相依”之意。《左传·僖公五年》云:“谚所谓辅车相依、唇亡齿寒者,其虞虢之谓也”辅,颊骨;车,牙床,比喻二者关系密切。“城阙”乃成都;“三秦”乃长安,两者搭配是辅车相依之关系,意思是成都城阙像长安城般巍峨高耸,在成都城楼上能望见郊外的五津。这是可能的,杜甫在成都西郊浣花溪草堂闲居时写下了名句“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。”诗人在成都城里低处都能望见一百七十里外的高处大邑西岭雪山,那么王勃在成都西郊城楼上也是能依稀望见三十里外的五津之首“白华津”的。可见“城阙辅三秦,风烟望五津”不是分指长安和蜀地之意,就是指成都。左太冲《蜀都赋》记成都“既崇且丽,实号成都华阙双邈,重门洞开。”用“城阙”当之无愧。另外,长安城外有三秦相辅,据《史记》“项藉灭秦后,分其地为三,名曰雍王、塞王、翟王号三秦。”而成都城外亦有三州相辅,蜀州、彭州、简州环伺而佐,这三州唐以前均曾号郡(《四川通志》),其规模与设置等同长安,故“城阙辅三秦”未尝不是比喻成都之壮丽。又,《华阳国志·卷三·蜀志》云“益州以蜀郡、广汉、犍为为‘三蜀’,土地沃美,人士俊乂,一州称望。”左思《蜀都赋》:“三蜀之豪,时已时往。”故成都配得上“城阙辅三秦”的赞语。即便是今人认为的“城阙”指长安,也是以长安比成都,送人之地也应是成都。因为一是王勃来自长安,心念长安,就会把成都比为长安,在成都送友就会说“城阙辅三秦”,二是表现了诗人对成都的喜爱,更愿意把它看成是梦萦魂绕的长安,以麻痹自己客剑南的事实。
又,诗中有句称“与君离别意,同是宦游人。”何能算“游”,宦游有二指,一是作宦后离家在外,一是在官场日久,升沉不定。按王诗游者应当在外,如一在长安,一在四川,更不能说“同是宦游”;再作推想,王勃此时若未游蜀,何以能描绘出蜀地风物,所以,若以“城阙”必指长安而勃必在长安送友,显然违背诗意。
自然,关于该诗的系年,就该在入蜀之后。因为若定诗写于长安送人入蜀时,证据不足,王勃不久也巧合入蜀,似乎太戏剧偶然性。诗写于入蜀后成都送人去蜀州,顺理成章更合逻辑必然联系。退一万步讲,就是有在长安送杜少府之事,那时王勃也还未履蜀地,不熟悉小地名蜀州“五津”是自然,故而该诗写作必于熟悉蜀地地方称谓“五津”后方可为之,这样诗的系年就必于入蜀后,为诗人在蜀地想起当年长安送杜少府入蜀的补记。故此诗写于总章二年()入蜀之后是没有问题的。
王勃有《入蜀纪行诗序》云:“总章二年()五月癸卯,余自常(长之误)安观景物于蜀,逆出褒斜之隘道,抵岷峨之绝径。超玄溪、历翠阜,迨弥月而臻焉”。他又有《春思赋》云:“咸亨二年()余春秋二十有二,旅寓巴蜀。”逆推二年,可见他入蜀时二十岁,风华正茂,履历蜀地山川,描绘形胜,诗序碑文都写了不少。这首诗的首联就是王勃对蜀地山川形胜的概括描绘,“城阙辅三秦”,似为诗人的借喻,描绘成都城的巍峨。那么,能“风烟望五津”,即川西平原,疑诗人可能就在“城阙”能比拟长安的成都,方可遥天展望五津。所以,这首诗首联矛盾的统一,极可能就是证明作者在成都送友人杜少府之作。首联的蜀地风物确定了,若以为入蜀前他就能这样描绘,又如何可能呢?确定了五津就在蜀州,诗题又何能称用蜀川?
作者简介:张起,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。
文//来自于《中华文化论坛》年02期。
说明
感谢原作者的辛苦创作,由于种种原因,我们在推送文章时未能第一时间与作者取得联系,如涉及侵权问题,请作者及时将意见建议发至邮箱bashuquanshu
.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lygangv.com/jbzl/13508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