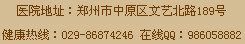![]() 当前位置: 甲型病毒性肝炎 > 疾病用药 > 学者论文林向蜀酒探原巴蜀的ldqu
当前位置: 甲型病毒性肝炎 > 疾病用药 > 学者论文林向蜀酒探原巴蜀的ldqu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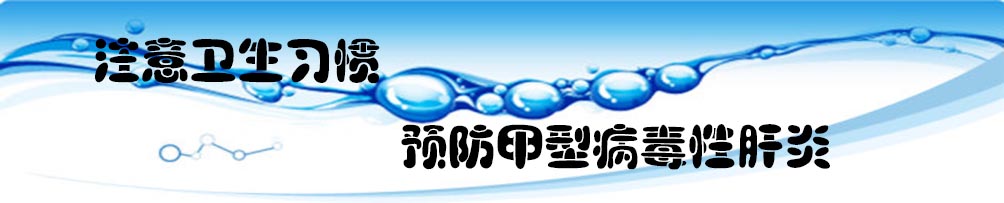
![]() 当前位置: 甲型病毒性肝炎 > 疾病用药 > 学者论文林向蜀酒探原巴蜀的ldqu
当前位置: 甲型病毒性肝炎 > 疾病用药 > 学者论文林向蜀酒探原巴蜀的ldqu
蜀酒探原——巴蜀的“萨满式文化”研究
林向
三星堆遗址出土大量的陶、铜酒器具,反映了古代蜀文明中酒文化的茂盛,它作为中国文化中的一枝奇葩,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。正如西晋张载《酃酒赋》所说:“物无往而不复,独居旧而弥新,经盛衰而无废,历百代而作珍。”今日巴蜀美酒香飘四海,正可谓源远流长。这里要探索的是另一面,即从蜀酒探原中可以体察到古代蜀文明中有灌溉农业的存在;还存在着古代世界共有的“萨满式文化”现象,但它又有其独特的古蜀风貌。
一、酒与巫术
巫术是一种古老的准宗教现象。原始人幻想依靠“超自然力”对目的物施加影响或控制,以达到自己的愿望,当时神灵观念还极其模糊。法国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野兽的图像上布满的刺痕,中国山顶洞人尸骨上撒布的红色粉末,被认为是原始巫术的遗迹。原始宗教产生后,巫术继续流行,有的宗教仪式就是巫术活动。巫术一直流传到现在社会。
酒,如果指含酒精(乙醇)的饮料,其出现当不比巫术为晚。民族志材料证明酒并不一定要粮食酿造,热带的原始部落把棕榈树砍倒,斜支在火上烘烤,树汁从切口流出,用葫芦装起来,放在有盖的容器里,自行发酵三至四天即成冒出泡沫的棕榈酒。潘格威人的酒葫芦里会发出“令人难忘的奇香”。专家们相信旧石器时代过着采集经济活动的原始人,从观察自然发酵的野果,到喜爱食用含酒味的野果,再到有意识地让野果发酵,是完全可能的。酒,是人制作的饮料,首先是人自己享用,其次也要让人所信奉的神灵歆享。
原始部落的宗教巫术活动,也就是全民的文化生活,主持者是巫师或部落首领,或身而两任。这种渗透着巫术的宗教仪式,往往是在歌舞狂饮中达到高潮。北美印第安部落,用仙人掌类植物酿酒,帕帕戈人每当酿酒季节一定要举行一系列庆典,同时巫师要举行祈雨巫术。印度康代人用一种叫Salopoogaxo的棕榈树酿酒,当开花时节他们除饮酒外啥事不干,这是一个无节制的狂欢和跳舞的季节。这种狂舞祭祀的场面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物中也有发现,如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陶盆上画着五人一组,连臂甩尾而舞的图像。甘肃秦安大地湾大房子(F11)地画中,两个巫师,左手叉腰,右手举顶,双腿交叉,正围着陈牲的俎案祭祀舞蹈。原始的酒文化浸透了巫术的魅力。
中国古代文人好酒,如有名的竹林七贤、李白、杜甫等等。在历代的诗文中,认为酒与宗教巫术不能分开。西晋张载《酃酒赋》写道:“嘉(杜)康(仪)狄之先识,亦应天而顺人。拟酒旗于玄象,造甘醴以颐神。虽贤愚之同好,似大化之齐均。……漂蚁萍布,芬香酷烈。播殊美于圣载,信人神之所悦。”在他看来,传说仪狄、杜康所造的酒为贤愚同好,人神所威悦。刘惔的《酒箴》说:“爰建上业,曰康曰狄。作酒于社,献之明辟,仰郊昊天,俯祭后土。歆祷灵祗,辨定宾主,啐酒成礼,则彝伦攸叙。此酒之用也。”在他看来,酒是祭天祀地,人间成礼的好东西。
酒以祭祀不仅是神的需要,归根到底是人的需要,祭后的酒肉无疑由奉祭者享受,而且巫师们更需要酒,他们要借酒精之力达到昏迷状态而与神界交往。北方的巫师——萨满,在召请他们的神灵时就必须装酒疯,瑜卡吉尔人的萨满在作法时,“尖叫、唿哨、咬牙、脸上抽筋,见者无不战栗”。西南的萨满——独龙族的巫师叫“乌”与“南木萨”。据调查:“他们成为乌的征兆是常在酒后言行异常,像是发疯,又说又唱又跳,自称是崖鬼(凶鬼)几卜郎附在自己的身上或卜拉(灵魂)上。”所以祭崖鬼是“乌”的专职,祭祀前必须让“乌”把酒喝足,等于让崖鬼喝酒,而祭毕的酒肉,照例众人共餐之,据说:“凡属鬼所需的歆享,都是祭牲的卜拉”,所以祭牲的肉是归人自己享用的。据最近成为“南木萨”的独龙族青年自叙:年夏天一个午后,他饮酒时感到有艳丽的太阳鸟围着他不停飞叫,一连数天,后来看到上方出现寺庙,并排端坐着七个“南木”(半鬼半神的善良精灵),叫他当“南木萨”,此后他只要有求,备上米酒鱼肉“南木”就会来帮助他。在这些巫师说来酒有通神鬼之功,又有贿赂鬼神之力。可见,酒与巫术有不解之缘,原始的酒文化必定打上“萨满式文化”的烙印。
巴、蜀的酒文化同样与萨满式文化有密切关系,这可从巴蜀的巫书——《山海经》中看出。鲁迅先生说:《山海经》“记海内外山川神衹异物及祭祀所宜”,“盖古之巫书也”。据吕子方、蒙文通先生研究:《山海经》的《海内经》四篇所说的“天下之中”指今四川西部地区,故这四篇“当作于蜀中”。《大荒经》五篇曾四次提到“巫山”,有关“巴国”、“巴人”的记载也仅见于此,所以,这五篇“可能就是巴国的作品”。考证精确可从。过去,专家们讲中国古代的萨满式文化必定要提到《国语·楚语下》中观射父论“绝地天通”一段。而笔者以为:颛顼命重、黎两人“绝地天通”的故事很可能出于巴、蜀巫师的传说。
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说:“大荒之中,有山名日月山,天枢也。吴姖天门,日月所入。有神人面无臂,两足反属于头上,名日嘘。颛顼生老童,老童生重及黎。帝令重献上天,令黎邛下地。下地是生噎(嘘),处于西极,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。”袁珂先生认为:其中“帝令重献上天,令黎邛下地”可能是韦昭注《国语·楚语下》:“言重能举上天,黎能抑下地”的同义语,“献”有“举”义,“邛”或为“抑”之误,其说可从。《山海经》保存了“绝地天通”神话的原始面貌是毋庸置疑的。
这名叫“日月山”的“天枢”就是萨满式文化中所说的“天梯”或“地柱”(axismundi)。这种“神山”在巴地有好几座。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说:“大荒之中……有灵山,巫威、巫即、巫盼、巫彭、巫姑、巫真、巫礼、巫抵、巫谢、巫罗,十巫从此升降,百药爰在。”这巴国的十个巫师能上下天地采药治人间疾病。《海内经》说:“华山青水之东,有山名肇山,有人伯高,伯高上下于此,至于天。”《海外西经》说:“巫成国在女丑北,右手操青蛇,左手操赤蛇。在登葆山,群巫所从上下也。”看来,以山为“天梯”、“地柱”的都与巴有关。
蜀地通地天的“天梯”是神树,如《山海经·海内南经》与《淮南子·墬形》所记的“建木”和“若木”,其说详下节。《大荒西经》载:“有氐人之国(氏原作互,依郝懿行改),炎帝之孙,名曰灵恝,灵恝生氐人,是能上下于天。”蜀蚕丛氏就是这种能上下于天的氐人。这神话大概反映古代的蜀王既是巫师祭司,又是政治军事首脑的历史事实。这与巴地巫师采药行医又略有不同。但是巴、蜀均善酿而好祀则是一样的。
二、“巴乡清”与蜀酒“醴”
巴人好祀善酿。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记其诗曰:“川崖惟平,其稼多黍,旨酒喜谷,可以养父。野惟阜丘,彼稷多有,嘉谷旨酒,可以养母。”其祭祀诗曰:“惟月孟春,獭祭彼岸,永言孝思,享祀孔喜。彼牺惟泽,蒸命良辰,祖考来格。”《水经注·江水》:“江之左岸有巴乡村(今四川云阳奉节间),村人善酿,故俗称‘巴乡清’。”盛宏之《荆州记》:“南乡峡西八十里有巴乡村,善酿酒,称‘巴乡酒’。”这种用黍、稷酿造的“巴乡清”酒既用来奉养父母,也用来享祭鬼神,而且名气颇大。据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载:秦昭襄王时(公元前-前年),白虎为害秦、蜀、巴、汉等四郡,秦王悬赏杀虎,有朐忍(今云阳)的巴夷廖仲药、何射虎、秦精等用白竹弩从高楼射杀白虎。秦王不敢爽约,除免其租赋外,刻石为盟曰:“秦犯夷,输黄龙一双;夷犯秦,输清酒一锺。”把黄金铸造的一对龙与“巴乡清”一锺酒相提并论,一方面说明秦王对巴夷的优待;另一方面这种名酒身价之高亦可见一斑了。清酒,按郑司农注《周礼·酒正》讲:“清酒,祭祀之酒。”贾公彦疏曰:“清酒……冬酿接夏而成。”一般醪糟酒是“冬酿春成”,可见清酒是一种久酿而成,含酒精度数高,味厚,滤去糟滓澄清的好酒。可惜,这种价比黄金的好酒“巴乡清”早已绝响于世,不知哪位有心人能“独居旧而弥新”加以恢复继承呢!
蜀之古酒也已失传。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载:到鳖令之后“九世有开明帝,始立宗庙,以酒曰醴,乐曰荆,人尚赤,帝称王”。这种叫“醴”的蜀酒,也是用于宗庙祭祀的。“醴”本是中原商周王朝用“曲蘖”(据方心芳先生研究是一种发霉发芽的谷粒,即散曲)酿造的糖化度大而酒化度低的连糟滓的薄味甜酒。《周礼·清正》把醴作为“五齐”之一,是供祭祀专用酒。不过,这里的“醴”似乎是蜀酒的专名,音译为“醴”与中原文献记载的醴不同。因为常璩说“以酒为醴,乐曰荆”,是说开明帝把酒叫做“醴”,乐叫做“荆”,中原有叫“醴”的酒而无叫“荆”的乐,可见两者都是蜀语音译。蜀酒“醴”与中原的醴不同,并不是“汁滓相将”连糟食用的薄味酒,其说详后。
巴蜀地区自古以来农业发达,酿酒谷物来源丰富。巴人用黍稷酿制旨酒“巴乡清”。那么,蜀人呢?!他们酿酒的谷物种类,一定更多。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载:“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,后稷葬焉,爱有膏菽、膏稻、膏黍、膏稷,百谷自生,冬夏播琴。”“都广”为古蜀地,即成都平原,在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注和《艺文类聚》卷八十五与九十引均作“广都”,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记汉武帝元朔二年(公元前年)在蜀郡郡治附近三十里地设置“广都县”,所以杨慎《山海经补注》称:“黑水广都,今之成都也。”后稷乃古之农神,《逸周书·商誓》:“在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谷,登禹之绩,凡天下之庶民,罔不维后稷之六谷,用蒸享。”传说农神后稷之葬地,当然是一个农业发达的中心地区。这里冬夏四季均宜播种,百谷滋生,酿酒的谷物绝不致匮乏。蜀人可能有麦,广汉三星堆早蜀文化遗址红烧土块里有许多禾本植物茎叶印痕,叶面窄而叶脉清晰,尚待鉴定。在一件陶豆的圈足上有一周花纹,是互生的肥大籽粒,如麦穗。据《左传》宣公十二年冬载:楚子伐萧,军队受寒湿,楚臣申叔展问:“有麦曲乎”。孔颖达疏曰:“麦曲作酒之物。”早蜀文化中酒器甚多,用麦曲作酒也是有可能的。《战国策·楚策》张仪说:“秦西有巴蜀,方船积粟,起于汶山,循江而……”积粟之盛,也许是酿酒的重要谷物。《礼记·月令》在总结酿酒生产经验六诀时,第一就是“秫稻必齐”。粘稷、稻米都应是重要的酿酒名物。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:“绵水,出紫岩山,经绵竹入洛,东流过资中,会江江阳。皆溉灌稻田,膏润稼穑。是以蜀人称郫、繁曰膏腴,绵、洛为浸沃也。”雒即雒水,今流经广汉三星堆-月亮湾遗址的鸭子河即古之雒水。成都平原与沱江流域为盛产稻之乡,古今一样。在嘉陵江流域的方山丘陵地区又有梯田,《华阳国志》载巴西郡、涪、郪、广汉、德阳一带均有“山原田”,与“平稻田”不同。到秦汉之世、“壅江作堋”,“灌溉开稻田”则更加普遍。
名酒(巴乡清与蜀酒醴)的出现,必有发达酿酒业,就必有发达的农业生产为基础,就必有发达的酒文化。考古发掘资料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
三、三星堆遗址所见的酒文化
广汉三星堆-月亮湾遗址自年发现以来,半个世纪中许多中外学者都曾在此做了大量的田野工作,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。近年来的发掘有新的突破,尤其是年3-5月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与省、县文物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的发掘,进一步证明了这里方圆十二公里的范围内,很可能是早期蜀国的一个重要都邑所在地。有的地下文化堆积层厚达2.5米,可划分为十六个文化层,根据地层学与器物类型学的分析,可分为四期:第一期出土物为新石器晚期的东西,是先蜀文化,即蜀文化的前身。第二、三期的文化面貌与一期不同,是早蜀文化的堆积,从类型学排比得知年代相当于中原的夏商。第四期继续发展,达到鼎盛,即殷末周初。过去只知道一种异于中原的铜兵器与船棺葬是“巴蜀文化”,时代只相当于中原的春秋战国时期,现在把蜀文化的年代提前了,所以三星堆遗址的第二至四期应叫“早蜀文化”。
这中心部位方圆六公里的遗址群被人工堆积的土埂——“城墙”所环绕,形成东西约米,南北残存-米的城邑。这里出土的大量陶酒器有:盉、杯、尖底盏、觚、壶、勺、缸、瓮等;食器有:碗、碟、盘、豆、罐等,都出在城墙圈里、房星密集的生活区内。这里不仅有“木骨泥墙”面积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舍,也有面积超过60平方米穿斗结构大房子与抬梁结构的厅堂。房舍厅堂间还有道路沟渠相连,形成聚落。在这些房舍聚邑内不仅出土髹了漆的酒、食陶器具;还出乐器如石磐、陶埙等;各种精美的工艺陶塑:虎、象、牛、猪、羊、鸮、杜鹃、鱼、蛙;还有双手反缚跪坐的石人雕像;有雕花镂孔的漆木器,玉石礼器:琮、璧、圭、璋、矛、斧、斤等高档消费品。相反的缺乏农业生产工具,出土少量的小型窄条形石斧、锛等只是生活用品。由此可见:这里应该是一座文明古城的废墟,而不是一般原始村落的遗迹;这里属于一群脱离劳动生产的上层人物的活动场所;当时已有水平较高的农业生产,畜牧渔猎也很发达;已有谷物酿酒的技术和大量用酒的需要。
从遗址出土的陶器来分析,当时的酿酒技术不会低于中原。《礼记·月令》总结酿酒经验说:“仲冬之月……乃命大酋,秫稻必齐,曲蘖必时,湛炽必洁,水泉必香,陶器必良,火齐必得,兼用六物,大酋监之,毋有差贷。”三星堆出土的陶器中符合这些条件的酿造器皿可能是一种高领大罐。这种陶器高约40厘米,腹部圆鼓,上接粗壮的高领,直口,下腹部作反弧线内收,接小平底。我们知道,发酵的毛霉和酵母菌都是很敏感的低级生物,“陶器必良”是说要在陶器内造成发酵的良好环境。这种陶罐高领直口正宜封闭,既可避免杂菌入侵滋生,又可造成有利于发酵的厌氧条件。“火齐必得”是指温度的控制。毛霉与酵母菌繁殖的最适宜的温度是28℃-30℃,所以夏天气温过高难于控制,一般都在冬天酿酒,但气温低了要靠加温才能保持。这种陶罐下腹部成反弧线内收便于受热,小平底不稳却宜于埋在灶炕边热灰中保温。所以,我们把这种高领大罐命名为“三星堆式发酵罐"。古代蜀人虽不知微生物学,却能制出这种合乎科学的发酵陶器,其功能可与《礼记》所总结的经验相对应,诚可贵也。
这里的饮酒器是一种很有特色的觚和瓶形的杯,瓶形杯数量极多,形制也多,粗看犹如今日北方烫酒用的陶瓷酒瓶。典型器形是:平底(全器最大径在底部),腹壁向上斜收,束颈,有的加一圈附加堆纹,侈口似喇叭形。器形细长,高约13厘米,容量在毫升左右。这种杯子侈口便于啜饮,但残糟却难通过束颈,容量也嫌过小,似乎饮用去滓的清酒最为适宜。所以蜀酒虽称“醴”,只是音译,并不如中原“汁滓相将”的连糟食用。第三期以后,又出一种尖底盏,口径约10厘米、高约4厘米,第四期后作为主要饮具逐渐代替瓶形杯。
盛酒器有瓮、缸、壶。有种缸的残片厚约1.2厘米,腹径大于厘米。壶有多种:侈口小平底的;长颈圈足的;短颈长腹的等等。在盛酒器中舀酒必须用勺,遗址出土的勺把特别多,有空心也有实心的,勺把头雕塑成各种长喙鸟头、兽头和钩形,便于钩住盛酒器口,不致沉落酒汁中。
既是低度发酵酒,就需加温,遗址出土陶盉很多。这里的盉粗看与二里头文化相似,而显瘦高,封口管流,三款足成柱管状,似乎也不宜加温带滓的酒料。
我们在86GST探方的第四期文化层中发掘了灰坑H30,坑不大,满放着大小不等的21件瓶形杯、中间有一把盉,周围放着多件平底盘、豆、小平底罐等盛食器,似乎是一个酒餐具“贮藏柜”。
四、“祭祀坑”里的酒樽
城墙里面是上层人物享用酒宴的厅堂,外面则是巫师们用酒作法的场地了。
年7-8月,三星堆遗址又有新的重大发现。在三星堆土堆(祭坛)南外数十米的地方,连续发现了两个长方形土坑,一号坑4.4米×3.3米,二号坑5.3米×2.3米。出土了金、玉、铜、陶、骨器与整支的象牙(不是“纳玛象牙”!)等40多种一千余件(图一)。青铜器总重量接近一吨。其中最大的青铜立人像。身高厘米,座高90厘米;最大的青铜人面像,通耳宽厘米,额颌高65厘米,分别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立人、人面青铜造像。一次出土如此众多的纯金制品在国内也是首见,有厘米长的金皮“杖”、金面罩、金条、金箔等。时代约当殷墟时期。国内对这两个土坑的性质,专家们的意见比较分歧。大体上有几说:①祭祀坑说:坑内无尸骨,不是墓葬;器物与火烧的骨渣堆一起,不是窖藏;只可能是祭祀坑。②窖藏说:坑的形制与器物放置与中原商周秦晋等地祭祀坑不合,可能是灾祸猝起,主人窖而弃走。③被毁宗庙说:此乃战胜者“犁庭扫穴”结果。④陪葬坑说:附近或有大墓。笔者则认为:蜀文化是有别于中原文化的地域性文化,有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,不能用中原祭祀坑来硬套,这种合坑埋藏的情况,很可能是古代世界风行的巫术——“萨满式文化”的产物,大概是在附近场地上举行了巫术活动后的“厌胜”性埋藏。
这两个长方形土坑相距约20米左右,方向一致N35°E,与祭坛走向近直角。两坑坑壁整齐,填土夯实,坑内堆积乱而有序。所以它们与城邑里居民的信仰有关,都是为着某种神圣的目的,有意识的作为。
坑里的包含物是经过搬运后有意识堆积.的。如一号坑的象牙、铜器、金器、玉器等与铡碎焚烧过的动物骨(可能有人?!)牙齿、打碎的尖底盏、豆、盘等陶器相混,从坑的东南角倾倒入坑的,从烧化黏结的情况看是燔、燎的遗迹。二号坑是依次放置的:玉器、铜戈和大小铜人像放在下层;40多具人头像环置四周坑壁下;上面由南向北依大小放着20多个青铜面像与铜尊、铜罍等;在上面放整支的象牙六七十支,填土夯实致使位置移动,但仍能看到乱而有序。
陶酒器被打碎了,尚待清理。一号坑的铜酒器也相当破碎,二号坑的铜酒器有尊和罍,还可能有方彝(?)。有些圆铜尊形体高大,花纹繁缛,肩头四个牺首(牛),上面各立一鸟,牺首间又有四只较大的立鸟。器表满饰云雷纹和饕餮纹,可以叫做“八鸟四牛尊”。器形与商周铜尊相似,而圈足改外侈为内收。与遗址出土的圈足陶豆相同,纹饰排列也与中原似是而非,它们是蜀人铸造的酒器。铜罍饰凸弦、云雷、饕餮纹,大的有牺首(牛)衔链环,有的表面光洁,呈青灰光泽,至今无半点锈斑,可见蜀人铸造工艺的精良。出土时有的里面装着贝玉,甲骨文的“登”字,正是豆上一尊,尊中置玉(珏);有的里面已空无一物而有使用(盛酒?!)痕迹。在古人看来祭祀奉献的酒是“琼浆玉液”,非常珍贵的饮料。在二号坑底出土两件头顶酒尊的铜人像。尊上有盖,双手过顶捧尊,站在镂花的座子上,做供献状(见图二,1)。看来这些尊罍都是置酒设供的重器。那么这些酒器供奉的对象是什么呢?!
最大的铜立像,戴冠,鼓眼高鼻,倒八字浓眉,着长服披巾,右袒,下摆如燕尾下垂,下着长裙,身躯瘦高,赤足带环,站在座上,双手巨大,握圈,左下右上,如执奉献状,执物已失。另外小人像很多,有戴冠的,有不戴冠的,都是双手执物。有人称为神像,其实这些可能都是供奉者,而不是受供奉的神灵(见图三)。
青铜神树有三棵以上。其一有三脚架座,座的三面各跪一小铜人。树干挺立高约3.9米,树干上分丫权,枝叶茂盛,结的果实如卵而有托。丫枝上有许多人,兽、鸟、蛇、铃和圆形挂饰,还有一只昂首垂尾的公鸡。这大概就是古代蜀地萨满(巫师)们“沟通天地”的神树“若木”和“建木”了。《山海经·大荒北经》说:“大荒之中有衡石山、九阴山、洞野之山,.上有赤树,青叶,赤华,名日若木。”《海内南经》说:“有木,其状如牛,引之有皮,若缨,黄蛇,其叶如罗,其实如栾(卵),其木若蓲,其名曰建木。”《海内经》:“西海有盐长之国,有人焉鸟首,名曰鸟氏,有九丘,以水络之……有木,青叶紫茎,玄华黄实,名曰建木,百仞无枝,上有九欘,下有九枸,其实如麻,其叶如芒,大皞爱过,黄帝所为。”《淮南子·墬形》说:“建木在都广(即广都,指成都平原),众帝所自上下,日中无影,呼而无响,盖天地之中也。若木在建木西,末有十日,其华照下地。”树上的神人大概是太皞、黄帝等这些既是首领又是巫师能上下于天者的造像,圆形挂饰可能是树上的十日,花果枝叶,乌鸡黄蛇竞都能一对照,而且在坑南壁下,最大的铜面像侧边就有一个巨大的铜鸟头像,高60厘米,正是“有人焉鸟首,名曰鸟氏”的写照。
四五十个铜头像,有真人头大小,有的光头,有的编辫,有的戴冠,有的还带纯金面罩。头部中空,颈部以下前后两个尖,可套在身躯上(身躯已失),犹如今日的木偶头像。这些大概是半人半神的配角,反映蜀国是多民族的联盟,他们是各方“诸侯”,或者就是各部的守护神。
二十五个大小不等(均大于真人头面)的铜面像,有的眼珠柱状突出如螃蟹,有的鼻梁上镶嵌云雷突饰,有的鼓眼吡嘴做愤怒凶相,有的定睛咧嘴做欢欣状。每个面像四角和额头都有方孔,便于悬挂,若配上头躯,按比例算来都是二米以上到六七米的巨大神灵偶像,从面相来看似乎全是男性。笔者以为这些装配铜面的巨大神像才是祭祀坑里崇拜的偶像。这是我国继辽西红山文化发现泥塑女神头像后,更为惊人的古代偶像的重大发现,一泥一铜,南北对应。联系到川西与辽西有许多相似的文化因素(如石棺葬俗、相同的铜罍等等),确实令人震惊。三星堆出土的铜神像,数量之多,形体之大,雕塑之精美,相貌的诡异实在超出人们的想象。可以断言,这至少是包含着天神、地衹、人鬼、图腾在内的、一种多神的、偶像崇拜的原始宗教的遗物。祭祀坑里的酒樽就是奉献给这些神鬼的。
奇怪的是这些偶像和神树都是毁坏后埋藏的,这大概与“厌胜”巫术有关。我们知道,原始宗教的灵物和偶像也可能遭到蔑视和责罚的。民族志材料告诉我们,有些原始部落认为不灵验的灵物可以抛弃另找代替,也有可能被打击,丢弃或烧毁,例如奧斯弟亚人在出猎不获时,就要责打偶像。坑里的酒樽与失宠的神像大概也是如此被埋入地下的。
至于神像为什么会失宠呢?已不可深究,但笔者颇疑此事与蜀地洪水及战乱有关。根据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记载:杜宇时国力达到鼎盛,而遭水灾,“其相开明决玉垒山,以除水害,帝遂委以政事”,“帝升西山隐焉,时值二月,子鹃鸟鸣,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”。常璩一介儒士,对民间神话往往改纂。但至少可以反映三个事实:①杜宇时洪水灾害极酷烈,《蜀王本纪》说:“若尧之洪水”;②因灾而变,改朝换代;开明乃荆人鳖令,简直就是“异族人侵”;③杜字下台是被迫的,蜀人才会悲子鹃鸟鸣。三星堆遗址三区第七层是一层厚约20-50厘米的淤土,青黑色,包含物极少,此层以上出晚近物。第八层相当于第四期,股末周初,正是祭祀坑的年代。这大概就是巫术厌胜埋藏的缘由吧?神灵不能制止洪水,只好埋入地下;开明治理了水患,就取得了政权,这就是地下酒樽的谜底。改钥换代更需要行巫术以厌胜,以求革旧布新。
五、巴、蜀铜酒器集锦
众所周知,世界文化宝库之上乘的殷周青铜器中,酒器之多“确实超绝古今”、“在古代世界中是没有先例的”。据《殷周青铜器通论》的分类统计,在五十类铜器中,酒器要占二十四类,将近一半。分为煮酒、盛酒、饮酒、挹注、盛尊五门,有爵、角、斝、盉、鐎、尊、鸟善尊、觥、方彝、卣、罍、壶、瓶、罐、缶、、卮、皿、区、觚、觯、杯、勺、禁等二十四类,绝大部分是祭享鬼神的“礼器”。这些酒器都有华丽繁缛的装饰,其中以各种动物图像最突出,不仅有自然界存在的:犀、鸮、兔、蝉、蚕、龟、象、鹿、蛙、牛、水牛、羊、熊、马、猪等;还有神话中存在的:饕餮、肥遗,夔、龙、虬等。这是因为“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实际上是当时巫觋通天的一项工具。”“现代比较原始的民族里面还有巫觋名为萨满的;萨满的主要作用便是通神,而在他们通神的过程中各种动物常常作为他们的助手或是使者”。周承殷制,原始多神宗教更加发达,仪式和祀典也更加规范。《国语·鲁语上》说:“凡禘、郊、祖、宗、报,此五者国之典祀也。”据《周礼·大宗伯》记载凡祭祀天神、人神、地祗的吉礼要举行:禋祀、实柴、燋燎、血祭、埋沉、副辜、肆献、馈食、祠、禴、尝、蒸等十余种仪式,而所有仪式都要“献”,“献者,献酒为主,献脯炙为从。”所以,酒是宗教巫术仪式中不可缺少的东西,殷商酒器之盛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。巴蜀文化中也有许多铜酒器,显然与殷周铜酒器有密切关系。
巴蜀铜酒器的出土,除三星堆外,已知重要的有:彭县竹瓦街殷末西周的窖藏;成都百花潭M10、新都马家木椁墓、大邑五龙船棺及土坑木椁墓(战国早、中期)、犍为金井等地的土坑墓、简阳糖厂窖藏、成都羊子山M、涪陵小田溪土坑木椁墓、青川秦墓、成都金牛坝土坑木椁墓、郫县土坑墓(战国早期);成都西郊土坑墓(战国末至秦灭巴蜀后);巴县冬笋坝及昭化宝轮院的船棺葬(自战国晚至西汉初年);可定为西汉初年的巴蜀墓葬还有成都南郊土坑墓、越西华阳村土坑葛、绵竹木板墓等。另外在新津、广元、峨眉等地也有零星的巴蜀酒器出土。这些发现中缺乏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的东西,这大概也是因为天灾人祸而造成的巴蜀文化的中衰现象吧!
巴蜀铜酒器的数量,初步统计已有一百余件。一般认为有罍、壶、尊、觯、钫、缶、彝(?)、勺等八种,笔者认为鍪应是煮酒器,故共九种。
罍是巴蜀常见的铜酒器(见图四,1)。著名的如竹瓦街窖藏出土九个铜罍,大的高79,小的高36厘米。饰以繁缛的饕餮、云雷、夔龙、鸟纹、蚕纹、涡纹等。而且都有主体的牺首(牛、百)、蟠龙。二号坑的大铜罍,还在饕餮纹上嵌绿松石。这些花纹较紊乱,有的甚至倒置,应是本地铸造的。辽西喀左县曾出土一件罍与竹瓦街同,疑由蜀地输出。也有直接从外地输入的,如新都马家墓出土五件一套的铜罍,肩有双耳,饰涡纹及三角蝉纹,与扶风齐家村出土的西周罍完全一样。
尊出在殷末周初的竹瓦街窖藏与三星堆祭祀坑。(图四,2、3)竹瓦街出土的饕餮纹尊与中原出土的亚丑季尊相同,为中原输人。而三星堆出土的八鸟四牛尊则是本地铸造。
方彝(?)残片仅见于三星堆二号坑。
觯只出在竹瓦街,牧正父和覃父癸所铸的器系殷人之物,可能与尊一道因蜀参加伐纣之役输人的。
壶出在战国墓中。新都马家墓出两套每套五件。都是盖上有纽,腹部有耳或铺首衔环,与楚文化的壶一样。成都百花潭出土的错银水陆攻战纹壶,堪称珍品,与故宫收藏陕西凤翔及洛阳中州路出土相同。三星堆遗址在第三、四期出了不少陶壶,其形制与涪陵小田溪及广元出土的两件银嵌错银卷云纹铜壶酷似,应是地方性的传统制品。成都南郊及越西华阳村西汉土坑墓则出蒜头壶,全是汉代文物之典型。
缶新都马家出土,扁体带盖,双耳带环,饰变体蟠螭纹。羊子山M出土的一件,无双耳而有提梁,三蹄足,原报告作委盉,其风格两地所出酷似。
钫羊子山M出土,与云梦睡虎地、耀县西汉墓出土相同。
勺绵竹西汉木板墓出土,柄已断,勺瓢椭圆形似耳环。
鍪指的是一种小口的釜形器。典型器形:小口、短颈、圆腹、圜底,肩部有一至两个辫索耳,单耳鍪可早至战国早中期,双耳鍪稍晚。这是巴蜀文化中富有特征性的器物之一。李学勤认为它与鍪甑一样,“它们的发祥地可能是巴、蜀,秦灭巴、蜀后传到秦,再流布到其他地区”,“应当认为是古代巴、蜀人民在文化史上的一次贡献”。但是,鍪之为器,过去不见著录,建国后考古文物界把这种“小口的釜”称为鍪,其实不当。《说文解字》释鍪是“也”,释“似釜而大口者”。颜师古注《急就篇》:“鍪,似釜而反唇。一曰鍪者小釜类,即今所谓锅。”可见鍪不是小口釜,而恰恰相反是大口釜。据《正字通》释:“兜鍪形似釜而反唇,非炊具。”可以戴在头上的胃顶似鍪,所以鍪绝不能是小口有颈的器物。若按当前约定俗成所称的这种小口釜——“鍪”,则与釜的用法不同,不是一般炊具,而是煮酒器:小口只占腹径的三分之一强,炊煮饭、肉是不便取食的;器形比釜小,百花潭M10出土的一件口径不到8厘米、高10厘米,做煮水器也嫌小了;凡墓中出鍪的必有釜、甑同出,可见用途不同,前者煮酒,后者炊饭;醪糟酒需煮食,小口的鍪倾汁留滓比较合适。可见,鍪是战国后新出的巴蜀铜酒器。
由此可见:
(1)殷末周初巴蜀铜酒器以罍、尊为主,仿自中原而有强烈的地方色彩。到战国以及以后基本上采用秦、楚的酒器。而还有自己的特色者酒器——鍪,且外传秦楚;反映巴蜀文化到东周已逐渐与华夏文化互相融成一体了。巴蜀酒文化同样是中国酒文化的有机构成之一。
(2)彭县竹瓦街窖藏是罍、尊、觯等酒器与戈、戟、钺、矛等兵器同置陶缸内。简阳糖厂的窖藏把戈、矛、剑、斤、钺等兵器放在铜罍里、上扣一铜盘而窖起来。在这些窖藏者看来兵器与酒器同样至关重要,早期的蜀地也同样有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”的观点。
本文原载《南方民族考古》第一辑,四川大学出版社,年,收入林向:《童心求真集:林向考古文物选集》,科学出版社,年,第-页。
责任编辑:秋雨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lygangv.com/jbyy/13498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