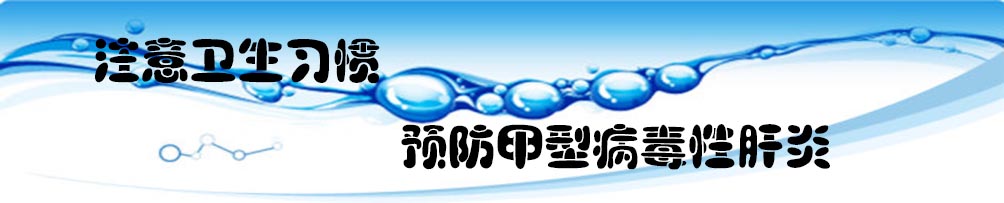最翔实、最生动、最厚重的叶圣陶传记。一个中国文化人的心路历程和道德风貌,一个真实勇敢、追求光明正义的叶圣陶。
《父亲长长的一生》作者:叶至善四川文艺出版社
陕西街的开明分店栈房是座典型的老宅院。门房朝南,租给了一家裁缝铺,看门的杂务就托付给他们了。进了门房是个狭长的天井。开明的书堆在坐北朝南的三间正屋里。天井东西两旁对称,都是相连的两组三开间平房,东边一溜分租给文化生活社和联营书店做栈房;西边一溜由我们家包了,工作和生活都在这六间房子里。父亲母亲的两张书桌相对,占了前一组的北头两间,有几把椅子可以接待客人。文协成都分会召开常务理事会,发起成立筹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会,讨论成立新世纪学会,出席的几位朋友凑我父亲的便,竟把会场搬上门来了。陕西街离少城公园和新书业集中区祠堂街不远,文化人闲逛喜欢走这一带,因而我家几乎客人不断。来客多就像电视机的频道多一个样,听到的方面就广,就可惜不能由着你按钮锁定,好的赖的都得听,兼听则明么,即使不顺耳,生气归生气,听不进去的也得耐着性子听,说不定还是作短文的上好的选题呢,可惜老有约定的文篇逼着交卷。在这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,父亲只好躲进后头的栈房,点上支洋烛埋头赶写他的。来客看到我父亲的书桌空着,回头就走了。会不会让正需面谈的朋友错过了呢?不会的,有我母亲守在那里呢,不会让特意赶来的客人白跑一趟。
在成都的两年中,开明总管理处召我父亲去重庆开过两次会。前一回是一九四四年八月半动身的,雪舟先生同行,前后四十天,为了商量开明在桂林的那部分人员和物资的撤退问题。其实已经迟了,日军已经从湘南攻入了桂东,开明有一批书籍、纸张,在半路上遭到轰炸,已经损失了大半;北撤的编校印制人员都历尽辛苦,分批陆续到达重庆。两年前在桂林相遇的文化出版界的朋友,如今又在重庆见面了,也有几位十年以上未见面的,如冯雪峰先生、叶以群先生、丰子恺先生,大多相见在会场上或宴席上。只谢冰心先生是初见。九月十九日下午,我父亲受邀去嘉庐拜访她,商量她的作品全部归开明出版的事。
后一回是第二年五月三十到的重庆。开明在第二天晚上开设计委员会,子恺先生、雁冰先生、巴金先生也是委员;主要开董事会讨论今后出书方向和明年纪念创建廿周年的事。没想到在这半个月里,父亲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,却是发起和筹备给雁冰先生祝寿。雁冰先生也是四十九岁。第四天,赵家璧先生邀请巴金先生和我父亲等数人同餐。叶以群先生说,本月二十四日将为雁冰先生五十岁祝寿,要我父亲拟一封邀请参加祝寿茶会的公启,再写一篇回忆文字。父亲立刻答应了,还建议邀集出版沈先生著作的各家书店,到那天一同发售他的著作,并在日报上刊登祝寿广告。邀请公启第三天上就交卷了,只三百字,请少数极熟的朋友具名;回忆文字写了约两千字,题目是《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》。离渝前两天,还替联合特价发售茅盾著作的各家书店做了广告。他心里牵挂着《开明少年》创刊号稿件的送审,到了那儿没能等到六月廿四,提前十天赶回成都了;只好在同一天,参加文协成都分会操办的茅盾祝寿会。祝寿会由黄药眠先生主持,有好几位先生致了辞。据记者报道,我父亲站到了凳子上大声呼喊:“我们要和茅盾一样提着灯笼在黑暗里行走。现在成都、重庆、昆明各地,到处有人点着灯笼,光明越来越多,黑暗终将冲破。”父亲冲动如此,好像又站在甪直的那片操场上,为五四运动而振臂高呼。在七月七日写给雁冰先生的信上,他为那天没能当面揖贺表示道歉,说“祝寿之事,弟近觉亦有意义,其意义不在于个人而在于社会。二十四日会,其给与相识不相识之友朋之振奋,实未可计量也”。
我父亲赶回成都,还为了主持文协成都分会的文艺讲座。这次讲座讲师堪称一流,佩弦先生正好回成都休假,也给拉了差。讲题二十四个,方面比较齐全;从七月九日开始,八月五日结束,共十四讲:
郭有守:文艺与教育姚雪垠:小说之创作朱自清:新诗之趋势叶圣陶:小说之欣赏许可经:音乐之欣赏邹荻帆:新诗之创作庞薰:工艺美术戴镏龄:传记文学吴组缃:生活态度丰子恺:艺术与艺术家吴作人:敦煌艺术姚雪垠:小说之结构陈白尘:戏剧之创作李劼人:佛罗贝尔
讲座设在燕京大学的一所大课堂里,是我父亲去向校长沈体兰先生借的,可容一百来人;听讲的不详,总之是文学青年吧。每次开讲,我父亲都去主持。结业的一天,讲师和百来个听讲的青年还开了半天座谈会。
讲座进行到一大半,沈体兰先生告诉我父亲说,燕大新近接到三青团中央团部的密令,说有奸伪分子在他们学校里设文艺讲座,所讲大多荒谬,要学校彻底查清呈报,又命它的成都团部,另外组织一个讲座来纠正。要讲唱对台戏呢,口气倒不小,两位老人都感到可笑又可悲。过了两天,沈校长要尽地主之谊,请文艺讲座的全体讲师吃一顿饭。父亲跟朋友们商量了,回说十来个人不在一起,要凑大家有空实在不容易,只好心领了。附带提一句,潘公展这段时间正好在成都,可能跟讲座的事有点儿关系。
有一件事隔了一个甲子,恐怕没人记得了。那年七月,锦江发大水,城里的大小街道都淹了,屋子里也有四五寸深。水从地板下面噗噗地往上冒,连父亲也只好整天赤脚,祖母就没法下床了。成都被淹是从来没有的事,报纸上只说雨量过于集中,也没提集中到何等地步。有人议论说是修筑飞机场掘断了龙脉,这倒颇有道理。成都平原上的八个大飞机场,占用的都是平平展展的水稻田。这经过了两千多年修整的水利工程,这高高下下的成千上万条沟渠,堵塞的不知有多少,掘断的不知有多少,上游来的水系不知打哪儿走,哪有不闯祸的。飞机场是非修不可的,老百姓都明白。好在天亦无言,罪名让老天爷担着吧。大水还不妨事,接着来的是霍乱。不时听得门口裁缝铺里的小伙计喊:“又抬过一口了!”一口什么?一口薄皮棺材,污水还滴滴答答往下流,与街道上的积水同流合污。雪舟先生不知从哪儿弄来了防疫针,让我给开明的职员和家属都做了注射。我还赶紧查资料,给《开明少年》补写了一篇《霍乱》。
在陕西街,我们协助过一位逃跑的壮丁。就在至诚去重庆之后的那些天,隔壁的茶馆被迫歇业,门窗紧闭,把守严密,说是关押了一百多名壮丁,等候飞机去昆明的。往年壮丁分四次征集,抓来了就地开拔,从不进城。这一回大约因为滇桂吃紧,改为一次征足,可是运输机没这么多,部分壮丁就被暂时关进了城里的茶馆戏院。逃走的事时常发生,大多被军警捉住或击毙。少城公园中就有一个跳进了荷花池,被手持大刀的看守追上,骑在他身上,用刀背乱砍他的臀部。游人看了抱不平,拥上去把那个看守的脑袋按进了淤泥里。大家以此为快,到处传说。这天晚饭后,门前人声鼎沸,又喊“壮丁跑了!”跟着听得屋瓦上有脚步声,随即跳下一个人来,求我们放他一条生路。我们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,他就绕到栈房后边不见了。听裁缝店的小伙计说,隔壁茶馆的壮丁起哄,跑了二三十个。我们以为昨晚那个壮丁已经跳墙走了,谁知他在夹墙缝里整整躲了一天,到晚上才让我们发现,哆哆嗦嗦爬了出来。问他,他说姓黄,住在老西门外,制草纸为业,出来收账,被拉住了,身上的衣服和钱全被军官没收了,换上了灰布军服。我们拣了身旧衣裳让他换上,父亲给了些钱,叫他快走,他说走夜路怕又被抓住。我们让他在栈房里吃了饭,睡了一夜。第二天一早就不见了他的踪影。也不用我们再叮咛,祝他一路平安吧。
(图片、文字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,请联系删除)
往期回顾:
在甪直,读叶圣陶
叶至善:《父亲长长的一生》50
在甪直,读叶圣陶
叶至善:《父亲长长的一生》49
在甪直,读叶圣陶
叶至善:《父亲长长的一生》48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lygangv.com/jbyy/13486.html
![]() 当前位置: 甲型病毒性肝炎 > 疾病用药 > 在甪直,读叶圣陶叶至善父亲长长的一生
当前位置: 甲型病毒性肝炎 > 疾病用药 > 在甪直,读叶圣陶叶至善父亲长长的一生